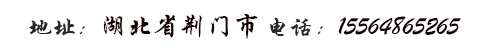小说阿根廷塞萨尔middot
|
经典文学作品分享 诗人最好的坟墓,是他词语的天空。 艾拉 狗 我在一辆巴士上,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突然,附近有条狗开始大声狂吠。我想去看它在哪儿。其他有些乘客也是。巴士上并不太挤:座位都坐满了,只有几个人站着;他们有看到那条狗的最佳位置,因为他们望出去的角度更高,而且可以看到两边。即使对坐着的乘客,比如我,巴士也提供了一个升高的视野,正如马之于我们的祖先:用法语说就是“PerspectiveCavalière”,等角透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巴士胜过轿车,后者的座位太低,太接近地面。犬吠声来自我这一侧,人行道这一侧,这很合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看不见那条狗,因为我们开得很快,我估计已经太晚了;我们应该已经把它甩到后面。它激起了通常会围绕某个事件或事故而产生的那种轻微的好奇,不过这一次,除了吠叫的音量,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什么事发生:人们在城里遛的狗很少叫,除了会对别的狗叫几声。所以这时乘客的注意力已经开始涣散,而突然它又被调动起来:狗叫声再次响起,比之前声音更大。接着我看见了那条狗。它正在沿着人行道奔跑,对着巴士狂吠,它跟在后面,全力以赴想追上来。这太奇怪了。在过去,在乡镇和城郊,狗会追着汽车跑,对着车轮狂叫;那是我小时候在普林格莱斯记得很清楚的场景。但现在不会了,似乎狗已经进化了,已经对汽车的存在习以为常。而且,这条狗并不是在对着巴士的车轮叫,而是在对着整辆车叫,昂着头,盯着车窗。现在所有的乘客都在看。难道是狗的主人上了巴士,忘了它或抛弃了它?要不也许是车上有人攻击或抢劫过狗的主人?不,这辆巴士一直在沿着督府大道开,好几个街区都没停,而只是在目前这个街区那条狗才开始它的追击。更复杂的假设——比如,这辆巴士轧死了狗的主人,或其他狗——也可以被排除,因为根本不可能。这是一个周日下午,街道相对较空:一起事故不至于会没人注意。 那条狗个头相当大,毛色深灰,尖尖的长嘴,介于纯种犬和流浪犬之间,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在我们正经过的地段,流浪犬已成为过去。它的体形还没大到让人看一眼就害怕,但也足以在它发怒时对人构成威胁。而现在它似乎就在发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绝望、发狂(至少就此刻而言)。驱使它的动力不是(至少,就此刻而言不是)攻击,而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想追上巴士,或者让它停下来,或者……谁知道? 赛跑在继续,伴随着狂吠。巴士加速前进,它刚在前一个街角被红灯耽搁了。它一路贴着人行道行驶,而那条狗也在人行道上奔跑,并渐渐掉到后面。我们已经快到下一个交叉路口,看上去追击会在此结束。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那条狗穿过了又一个街区,继续穷追不舍,它也在加速,同时狂吠不止。人行道上没什么人,否则像它那样横冲直撞,视线紧盯着巴士车窗,势必会把行人撞飞。它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响,震耳欲聋,淹没了马达声,充满整个世界。某件本来从一开始就该很明显的事最终浮出水面:那条狗看见(或闻到)了这辆巴士上的某个人,它正在追那个人。一个乘客,我们中的一员……其他人显然也想到了这点;大家开始带着好奇的表情环顾四周。有谁认识这条狗吗?怎么回事?是狗的前主人,还是它以前认识的某个人?我也在环顾四周,一边琢磨着,会是谁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后想到的人才是自己。这我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而且是间接地意识到。突然地,被一种依然模糊的预感所触动,我看向前方,透过挡风玻璃,我看到路上畅通无阻:在我们前方一长排绿灯几乎绵延到天际,预示着飞速而不间断的行进。但紧接着,随着我内心升起的焦虑,我想到我不是在出租车上:巴士每过四五个街区就有固定的站点。的确,如果站点上没人候车,车上也没人按铃要下去,巴士就会一路不停。就目前来说,车上还没人走向后门。运气不错的话,下一站也会没人。所有这些思绪都同时涌向我。我的焦虑感在继续增强——几乎就要发现那个不言而喻的结论。但这被当时的紧急状况推迟了。有机会让我们一直不停地开,直到那条狗放弃追击吗?我的视线只移开了几分之一秒,然后我又去看它。它还在狂追,狂吠,像着了魔似的……它也在看着我。我明白了:它是在对我叫,我就是那个它要追的人。那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够招致的恐惧感向我袭来。我被那条狗认出来了,而它正对我穷追不舍。虽然,一时情急之下,我已经决定否认一切,不供出任何事情,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它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因为我曾虐待过那条狗;我对它的所作所为,的确是,说不出的无耻。我必须承认,我从未有过十分坚定的道德原则。我不是要替自己辩护,但这种道德缺失可以部分解释为:从幼年时起,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战斗。这渐渐钝化了我的正义感。我开始允许自己做一些体面绅士不可能做的事。但也难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此外,我的恶行根本算不上真的犯罪。我并没有真正违法。但我也没有像个真流氓那样,把自己做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对自己说我会做出补偿,虽然我一直在想到底该怎么做。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以如此怪异的方式被认出来,被迫面对一段埋藏如此之深,以至于似乎已被遗忘的往事。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指望着某种免责。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做,都会假设,首先,一条狗只是一条狗,它的个性将会被其所属的物种所同化,从而最终消失。于是我的罪恶感也会随其消失而消失。曾有片刻,我可鄙的背叛赋予了那条狗某种个性,但那只有片刻。而那片刻居然持续了这么多年——这里有某种超自然的、令人惊骇的东西。不过,当我再仔细想想,一丝希望出现了,而我立刻就抓住了它:时间已经过去太久。狗活不了那么久。如果我把年数乘以七……这些念头在我脑海里翻滚着,与那变得越来越响的、沉闷的狗叫声相互撞击着。不,说时间过去太久是不对的;这种算法只是我延迟自欺的一种方式。我最后的希望是当你面对某种太过严重而无法承受的状况时,那种经典的、否认一切的心理反应:“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我在做梦,我肯定有哪里搞错了。”而这一次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反应;它是真实的。真实到我不敢去看那条狗;我害怕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我又太紧张了,没法装得若无其事。我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我大概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所有其他乘客都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uana.com/shael/6262.html
- 上一篇文章: 希梅内斯丨你与我之间,爱情竟如此淡薄
- 下一篇文章: 圣莲岛封闭施工今年八月来看不一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