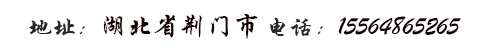布洛克教你写推理小说肆
|
《时空恋旅人》里头,男主角知道自己可以时空穿梭之后目瞪口呆地问自己的父亲:那,你都用这个技能干了点儿什么?老爷子笑着说:我看书啊。我把一个人一辈子能看的书都看完了。 这是事实,当你拿着书站在即使是拥挤不堪的地铁,你也会感到时间倏忽而过。承平盛世有敲击乐,英雄末路四面是楚歌,霸王和虞姬的故事正看到一半就不得不下车。世上有男人,有女人,有悲欢离合,有恐惧,有哀伤,有担忧,有豁出去的狠劲,就有食客。爱情和婚姻的纠缠你才看了一半,就不得不钻进被子蒙头睡觉。事实就是这样:对于看书来说,时间永远都不够。 今天,小编想继续跟你分享老布教你写推理的文章。因为在老布看来,事实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可惜啊,意气风发的时代,一去不回头。我现在连我一半的藏书都没读完,有一大堆书我看了开头两章,就往旁边一扔。这种转变,我想是来自于中年的自信吧。” 亲爱的乔: 如今,我相信你在大学里,已经安顿妥当了。我最近跟你老爸聊了一下,他在言谈之间,甚是得意,对你拿到奖学金这事儿,讲了几句外人很能体谅的吹嘘之词,同时,我也想在这里顺便向你道喜。 他提到你正在考虑当作家。讲到这里,我就不知道该致贺,还是致哀了。或者,我应该趁机说几句逆耳忠言。 第一个在我脑海浮现的问题是:一个未来的作家,要上大学吗?我念书的时候,想也没想,一头撞进英国文学系,既然我想写点什么,那么,最适合的去路,当然是搞清楚别人在这个领域里,做过哪些事情。 我用不着在这里假惺惺的抱怨,这种制式的教育对我的天才是怎样的扼杀,但我也想不出受这种教育,给了我什么好处。作家一定是读者,这点没什么好争议的。我这批靠写作过活的朋友,机会个个是书迷,但是研究文学跟阅读毕竟是两码事。在一般的学院里,课程多半是帮未来的文学老师做准备。这当然也挺好的,教书与写作并没什么互斥的地方。好些不大够格,又不想靠自由投稿过日子的人,会觉得教书是个挺安稳的行当。 建议你不要修英文的理由之一是:这科系可能强迫你去念一些你根本没兴趣的科目。念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追求你的利益,不要管你做的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也不要管那些事情好像跟写作生涯有很大的差距。坦白说,你念什么其实没什么差别——只要你想念就成了。人文、硬科学、历史、植物学、哲学、微积分。你现在是学生,将来是作家,只要能够搅动你的思维,在当下,就是最好的选择。 从“追求最好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推出一个逻辑:在学校里,哪个教授最能冲击你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教师。想尽办法,至少要上到他们的一堂课,别管他们在教什么。课堂上过分专业的知识、必读教材的内容,毕业之后,顶多在你心头晃荡一阵子,也就不见了。但是那种与特异心灵的智性冲撞与交流,却会跟你一辈子。 没有人可以教你写作,在教室里没有,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但是上写作课也并不等于浪费时间。 相反的,它提供了时间这种资源——这就是上写作课的最主要的功能。你因此有很多时间,坐在打字机前面,进行你的文学创作实践,最后还给你学分。喜欢创作的你,可能要从别的课程里偷时间来写作业。选了写作课,老师就会要求你花一定时间在写作上,这种压力很有用,作业一大堆、要求很严格的课程,常常会让你有最丰硕的成果。 大多数的写作课程会要求你交一篇习作,由老师或是你自己大声念出来,交给每个小组进行批评。有机会的话,我真希望这种教法能改善一下。小说的句子,有时感情、深度是念不出来的,跟印在纸上的效果,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有这些遗憾,写作课对你来说,还是很珍贵。你不但可以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有很多的机会,观察同学写作上的弱点。 这的确非常关键。从阅读中学写作,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就是逼自己去读一大堆生手的拙劣习作。把它们的缺点照出来,要比你琢磨那种玲珑剔透、浑然天成、无迹可寻的杰作,要有用得多。我曾经在一家文学经济公司上班,每天被迫去看一大堆不请自来的稿件,但在那几个月里,确实我写作技巧突飞猛进的阶段。每天,我从成山的文字炼狱中挣脱出来,晚上回家写作,我就知道该避开哪些错误。 多多体会同学灌注在习作中的心思。每一页的情节铺陈、角色对话,要看仔细,倾听作者的心声,就是最好的教材。接受别人的批评,管它是老师的指导,还是同学的胡乱嘲笑,听着就是了,就像是在菜里倒一堆酱油一样。听得不顺耳的话,笑笑就算了,未来,这门修养还要协助你面对编辑与出版商的冷言冷语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选修写作课,但我希望你在大学中,能尽量抽空写作。至于你到底写多少,这个嘛,当然由你决定。 不管校内校外,每个想当作家的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也在追求不同的目标。有的人觉得他有独特的观点与省思,要在小说中,呈现出来。有的人最重要与最终的目的,是当一个知名作家,写作,只是他们追名逐利的工具。 如果你是第一种人。那么我能给你最好的建议是——不要听别人的建议,就连我的话也一样。光凭直觉,你可能就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么,去做吧,踏着你的节奏,锁定的目标,尽可能的从容、舒缓的展开你的笔触,寻找对你来说最合适、最自然的题材与表现形式。 商业上的考量,能少,就尽量的少。在大学时的作品,绝少,无论在商业上或是艺术上,绝少会取得什么成就。也许你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意外,但是,你在未来四年,单靠一部打字机就名利双收的机会,真的是微乎其微。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你可以完全甩脱商业的羁绊与世故的算计,至少目前你还可以随心所欲。 也许你主要的兴趣,是想满足市场的需求。也许你只想成为一个畅销作家,一个职业的文字匠。即便如此,你也不必妄自菲薄。你的作品未必毫无艺术价值,顶多就是你的出发点不一样而已。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大概没法想象我多讨厌听到这种论调——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的作品印出来、在支票上看到我的名字。在我确认写作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之后,我迫不及待的往前冲,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 如果你跟我一样狂热,也许有些建议就没那么荒谬了。首先,尽可能的写作。写得越勤快,你就会越快养成发展构想、化思考为作品的习惯。 研究市场。即便你的作品以市场为导向,你作家的这块招牌,也不会因此显得廉价。你不该随波逐流,揭露隐私的忏悔录、青少年犯罪小说,市场流行什么,你就写什么。你应该广泛阅读各种小说杂志,直到你发现某种类型你写起来很享受、很自豪为止。如果你读某种类型觉得索然无味、当上某种类型小说作家,又让你无地自容,试问,你有可能写得好吗? 要有行家风范。打字行文之际,要学习并维持某种写作的格式。不断投稿。一写完,就寄出去,百折不挠。在我念大学的头两年,一点也不夸张,我收到的退稿信,可以贴满一面墙。除此之外,我根本没法证明我是作家——即便是一个不怎么成功的作家。这么一路走来,我也习惯了拒绝。但就有这么神奇的一天,一个编辑要我修改我的故事,随后买了下来,所有的辛苦好像就此有了回报。我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专业作家。 绝大部分的学校都提供各式各样有关文学或新闻的活动——大学报、文学杂志。对写作有兴趣的学生,通常会参加这种社团,并且获得很好的回报。但话要说回来,你选择这些活动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才行。参加课外活动的标准,跟选课的态度一样,都要能满足你真正的兴趣。 我在当大学报编辑的时候,得到了好些珍贵的教训。我懂得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把话讲清楚、如何在截稿压力下,交出作品,还让我跟自己保证:毕业以后绝不干记者。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收获,其实是交朋友。我上的大学跟你选的学校没什么两样,都是强调创作的文理学院,学生各具特色,老师古怪得可爱。跟这些怪人打交道,促进的个人成长与知识扩展,比课堂上学来的所有学问加总起来,还要游泳。我认识的作家,大概都少不了这一段经验——那些不写作的人,想来也一样吧,尽管影响深浅有别。 既然写作是你的最终目标,你或许会希望在毕业之后,可以靠写作赚钱养家。你可能会想,也可能有人会建议你:你最好培养某种专长,先干点什么实际的,才有闲工夫慢慢的朝写作之路发展。 不要浪费时间。在大学毕业以后,你可能会换好几个工作。还没成为职业作家呢,就先盘算要干那些混饭吃的事情,等于是准备迎接失败。现在的时间请用来成长、学习、写作、享受。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来伤脑筋。 好好玩阿,乔。我也不敢奢望你会相信我这一套,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怀念大学四年这段美好的旧日时光。尽情享受吧——同时感谢你提供我本月专栏的主题。 爱你的,赖瑞 有次,我应邀回安提阿学院带一堂写作课,见到久违的老友诺兰·米勒(NolanMiller)。 我曾经在他的写作工作室,开始小说创作的初步尝试,那当然还是小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率领骑兵队攻占圣胡安山(SanJuanHill)那年头的事(译注:卜洛克讲的是一八九八年爆发的美西战争)。 我们谈起学生,过去的,现在的。“他们都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天赋。”诺兰说,“天赋可没法保证成功。如果不能用纪律去发掘他的天赋,再才华横溢也没有用。虽然如此,每个人还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天赋。我总跟他们说,他们不缺天赋。” “为什么呢?”我怀疑。 “很简单,我根本没法分辨。有的时候,我看得出谁下笔很有点天赋,但是,没天赋的人没我可就眼拙了。我不知道谁没有成长、发展跟改进的能力。更何况,”他补充说,“要他们试着写点东西,也不是什么坏事。就算一事无成,至少在读书的时候,读得出一点门道来。” 好几年前,我听说过一个小提琴家的故事,可能是编的吧,我在第十二章“天赋的力有未逮”,再详细说这个故事。诺兰的说法温柔敦厚,使得我格外欣赏。 我们在写作上面下的功夫越深,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越能体会阅读的精髓呢?看起来这是比较合理的假设。如果自己身体力行,熟知实务的各种窍门,见到出自他人之手的相同作品,自然会有较为细腻深刻的体悟。我那些搞音乐的朋友,听音乐不一定是我这种想法,而我妈妈,在艺廊里看画作,也一定比我有更全面的理解,毕竟她自己作画,有好些年头的历史了。 这些原则在艺文界之外,当然也适用。运动转播的时候,经常找些老运动员来讲评,当然不只是借重他们的名气。自己亲身玩过,当然讲起来头头是道,比起你我来,不可同日而语。 讲到阅读,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有个不错的开始。我的作家朋友,个个悠游在印刷品世界里,阅读成痴,而且毕生如此,不知老之将至。唐·魏斯雷克有次承认:万一家里什么东西都被他读完了,他甚至会去研究伍斯特酱(Worcestershiresauce)瓶子上的成分说明。 这些年来,我曾经碰过一两个对阅读不怎么有兴趣的作家,但是极为罕见,几乎可以列入濒危绝种的动物名单里面。 我患了这辈子难以治愈的阅读饥渴症。在大学时代,读起书来,我有点像是青鱼在海里,撞上了一排鲱鱼,狼吞虎咽,饥不择食,伸手所及,不管捞到什么就往嘴里塞。我意志坚强,阅读量激增,乐此不疲,有点像是老烟枪逐渐适应手上的新烟斗,总觉得读到什么,都能让我的成长大幅向前、下笔更有韵味。即便不大喜欢我手上的书,我还是会摇摇头,硬着头皮把它读完,仿佛半途而废,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可惜啊,意气风发的时代,一去不回头。我现在连我一半的藏书都没读完,有一大堆书我看了开头两章,就往旁边一扔。这种转变,我想是来自于中年的自信吧。托比·史坦的小说——《永远》(AlltheTimeThereIs)的叙述者在过三十五岁生日之前立誓:自此以后,她绝对不要因为看了一本书的开头,就非强迫自己把它读完不可。誓言发得很有道理,在有限的生命里,这是很合理的时间运用。 我想,我之所以越来越会分辨写作的好坏,应该跟我的阅读态度改变有关。我日出而写,日没还写,一日复一日(请别介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格外能体会其他作家写作的技巧。只要一看开头,我立即可以察觉到这个作家的功力不足。我会处处提防、引经据典,根本没法放下对这个故事的质疑,自然无法安然享受阅读的乐趣了。 如果我的作家之耳告诉我,书里的这段对白矫情造作、粗苯不堪,我要如何相信讲这种话的角色?如果我的作家认知,不断的在提醒我:这段情节描述拖泥带水,我又怎么能浑然忘我,融入小说塑造的情境里? 许多畅销书,可能硬塞进大量媚俗的商业成分,编辑笑得开心,我的心头却可能是阵阵寒意。小说的故事可能不错,但只要我是惦记着它的斧凿痕迹,就没法享受纯然的阅读乐趣。 我不是说喜欢阅读这种类型作品的人,不该读得如此肤浅,自得其乐。完全相反,我非常的嫉妒他们。他们在书里,得到快乐的时光,而我,一个自诩的终生读者,却越来越找不到书可以读。 幸好这种事情,也是有补偿的。 一旦让我找到好作品,我可以同时享受不同层次的阅读乐趣。我可以放下身段,做一个肥皂剧的影迷,无可救药,奋不顾身的投进小说的情节中。故事有趣,我会哈哈大笑;情节哀伤,我会怆然泪下。我的职业感受,虽然百无一用,在这个时候,却会发挥加成效果,放大我的回应能力——但,这是作品写得很好的时候。 同时,我也会睁开我的作家之眼,分析一下作品动人的原因。不管我是多么投入主角的命运当中,我经常会允许自己冷静一下,研究作者到底是怎么营造出这种吸引力来的。在一本流畅的小说中,出现了坑坑疤疤的段落,我也会试着想想,是哪个地方走了调,让天籁般的合音,出现了刺耳的杂音。 在我阅读的某些时候,我甚至会在心里,重新把情节组合一遍。这段话是不是写得太长了?删掉某些反应,情节会不会更流畅?这个转折会不会太突兀了点?如果我们在这里喊“卡”,文字会不会更精简、感情会不会更有余裕? 你可能觉得用这种方法读书,等于是睁开一只眼睛睡觉,作家的自觉阻止了读者的投入。 奇怪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经常见到音乐家坐在观众席上,追着每一个音符,凝神细听,但我发现集中心思只会提高他们享受音乐飨宴的乐趣。同样的道理,在我琢磨出作家的写作技巧之后,也同样强化了我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这过程的另外一个面向,也不能说不重要。这些年来,我始终不曾中断对于写作的研究,因而发现两个可以让我们持续学习的地方——我的办公室与图书馆。我在写作中学习、在阅读中学习。这些年来,我的写作提升了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自觉:同样的道理,我阅读的著作与小说,也磨尖了我写作的技巧。 只要重读我在好些年前看过的书,我的改变幅度有多大,就一清二楚了。有时,这是非常沮丧的经验。年轻时期视若珍藏的小说,如今读来,完全读不下去。这当然不是因为小说变烂了,而是现在的我,是用不同的观点打量。我以前批判能力不强,没法用一个作家的眼光去回顾。我翻开过去心爱的作品,都要哭出来了,那是对逝去岁月的哀悼。 幸好这种失望,经常被出乎意料的喜悦弥补起来。有些老书,低吟再三,还是历久弥新——道理很简单,现在的我已经配备了作家的火眼金睛,更能体认作家笔下的奥妙。我每次重读奥哈拉(JohnO’hara)与毛姆(SomersetMaugham),都能发现他们写作上炉火纯青的技艺。几年前,我为了如下的几个理由重读了他们的小说与短篇故事——第一,为了纯然的阅读乐趣;第二,跟他们创作的角色叙旧;第三,体会这两个作家是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把生命、真理、美丽的光辉,洒在世人身上。 我还是会因为同样的理由,重温他们的作品。每多读一次,我就有更多的心得、更能掌握他们作品高妙之处与提升作品层次的方法。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我观察到毛姆运用叙述者的观点,像是指挥家手上的指挥棒一般灵巧。在我读过五六次《北费德列克十号》(TenNorthFrederick)之后,我还替周·查宾(JoeChapin)的殒落感到难过,但我可以很冷静的分析,奥哈拉是怎么从其他人的观点与叙事中,揭露主角的复杂性格。 我阅读的速度放慢下来了。以往我读书,总是急匆匆的,像是自律甚严的竞赛者。如今,我比较细吹慢打,咀嚼再三,反复体会,这才咽进喉咙。写作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读者,一如阅读也不断提升我的写作能力一样。 要怎样才能练就作家的阅读方法?很抱歉,我没有什么诀窍可以提供,不过,倒有个经验可以分享。我在读手稿的时候,会比读校样的时候疏离、挑剔。我在读校样的时候,又比我读成书的时候留神、谨慎。换句话说,越接近作家的打字机,作家的意识就越强,越让我格格不入。我心里很清楚:我在看某个人的作品,而不是什么山上的石碑。总而言之,读装订好的作品,我会比较自在,读手稿,我就比较提防。 顺道一提。我不知道你要怎样才能从作家的眼光去阅读作品。但只要你持续写作,持续阅读——这功力就自然而然的冒出来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ushanz.com/shagk/1047.html
- 上一篇文章: 7张图告诉你为什么会有传送门
- 下一篇文章: 碧桂园杯2017第十二届环岛赛参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