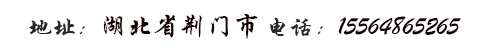Vol84亨特middotSm
|
我把一杯酒端到床上,“这里,”我说,“这个地方是让我厌倦的东西之一。”我将杯子塞到她手中,然后走到窗户旁边,望向外面的街道。“另外,主要是,”我说,“我厌倦当一个无赖——一个人形的喉盘鱼。”我笑出声,“你知道这种鱼吗?”她摇摇头。“这种鱼的肚子上,有一个吸盘,”我说,“然后他们会依附在鲨鱼身上,如果鲨鱼捕到了大餐,他们就可以吃鲨鱼吃剩的东西。”她咯咯地笑了,低头啜了一口酒。 前段时间迷上了朗姆酒,天天用可乐兑着喝,所谓“自由古巴”。在身体自由的时候,必须要注入灵魂的古巴,就找到这本《朗姆酒日记》,后来改编的电影由强尼·德普主演。 《朗姆酒日记》是作者亨特·S·汤普森的半自传小说,小说里弥漫着颓丧,迷茫,更重要的是朗姆酒的味道。你会想,什么样的人才写得出来这样又胡说八道,又令人无法辩驳的小说? 自杀前的汤普森 因为汤普森本人就是个疯子,青年时期经历过60年代美国的大变革,大部分时间他是一名美国记者,与所有的美国总统做对,“刚左”新闻写法的教父(一面胡说八道,一面说出事实真相,极具个性化的表达),年模仿海明威开枪崩了自己。 小说的主人公叫保罗·坎普,一位失败的新闻记者,在周游世界做过无数职业之后,来到加勒比海岸的波多黎各的一个小城圣胡安(感谢我的波多黎各外教,让我对这个地方不至于陌生,虽然一点也不了解),在《圣胡安日报》谋了一份差事。 这个小城有一个“艾尔”酒吧,报社的员工都常在这里喝酒,尤其是朗姆酒,加冰的朗姆酒。《日报》的员工几乎都是疯子:主编莱特曼总说自己的梦想是新闻自由,却总停留在口头;弗里茨·也门脾气暴躁,刚到报社门口,我就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群混混打架,后来证实那就是也门,而我在飞机上心仪的那个性感小个子女人切诺特,正是也门的女友;萨拉是圣胡安唯一的专业摄影师;莫贝里虽然是政法方面的记者,却是个十足的酒鬼,他最强的技能就会喝醉之后还能找到自己的车…… 《日报》内有各式各样的人,从试图想要把世界拧成两半,再重新来过的狂妄土耳其小伙子,到只想在一群疯子把世界拧成两半之前,过过好日子的啤酒肚老头。整个报社的确有些有才气又正直的人,但也有一些连张明信片也不会写、堕落无能的失败者,包括混混、逃犯和酒鬼,一个顺手牵羊、总是在腋下夹着一把枪的古巴人,一个半开化、有恋童癖的墨西哥人,流氓、人渣、人形脓包等等。对多数的人来说,工作只是为了换杯酒喝,或是凑足机票钱罢了。另一方面,也有像是汤姆·班德瓦兹这种天才,之后为《华盛顿邮报》工作,得了一座普利策奖,还有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了让报纸顺利出刊的泰瑞,现在担任《伦敦时报》的编辑。 如果这些年来曾经为报纸工作的人,同时出现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讲述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怪癖,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离谱行径,连上帝本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马上晕倒在地,不断拉扯自己的头发。 这几乎是“垮掉的一代”文学的通用设定,一群疯子,一个相对正常清楚的旁观者,一个美丽但不羁的女性,以至于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的想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还要美丽。她穿了双凉鞋,一件格子裙和一件白色无袖丝质上衣,但看起来最不同的是她脸上的表情,脸颊红润健康,因为流汗而湿润。她的头发蓬松地垂在肩上,眼睛发出兴奋的光芒,她现在看起来真是性感极了。她包裹在格子裙和丝质上衣里的娇小身躯,似乎蕴藏了无穷的活力,随时可能爆发。 最终切诺特被当地人民强暴,报社快倒闭时转让给别人,也门和萨拉因为生气主编莱特曼而心生杀意,在混乱之中打死了莱特曼,而我则掩护也门逃出了波多黎各…… 总之一片混乱,生活并没有越来越好。 拿手枪的汤普森 不过这本书的好处是,故事基本就在圣胡安一个地方发生,不用记那么多地名,而《在路上》则是在美国到处跑,光是记地名就是巨大的阅读障碍。因此《朗姆酒日记》读起来非常愉快。 另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点是《朗姆酒日记》几乎没有主线情节,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唠唠叨叨,基本可以随时拿起随时放下。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大篇的胡说八道之中,有一些话突然就会扎你一针,还有点疼。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有魅力。 所以情节就不讲了,摘录一些精彩的胡说八道。 来一杯朗姆酒的汤普森 但我心中也同样存有疑问:再这样下去,以后的生活一定一无是处,我们所有人都如演员一般,在毫无意义的漂泊中欺骗自己。一方面怀抱着无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为未来感到彷徨,我在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下,继续着这样的生活。 第一次,我意识到,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画出了一道长长的距离。 我来到的这个世界,有着一种奇怪又奇特的气氛,有些事情很好玩,但同时却矛盾地充满了沮丧。我来到这里,住在豪华旅馆,却坐在看起来像蟑螂,听起来像喷气式飞机的玩具车里,绕过半个城市;偷偷地从后门的小巷中溜走,却肆无忌惮地在沙滩上胡搞;在鲨鱼出现的海中猎捕龙虾,自己却被大批说着外国语言的暴民盯上。这些事情,发生在西班牙殖民的波多黎各,但这里的人却使用美金,开着美国造的汽车,坐在赌场中玩着轮盘,假装自己来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城市的某部分,看起来很像美国佛罗里达的观光胜地坦帕市,另一部分又很像是老旧的难民营。每个我看到的人,都好像是刚刚从某个重要的电影试镜会走出来似的。另外,我的薪水高得可笑,而我整天做的就是闲晃,然后去“熟悉状况”。 萨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永远可以联想到自己。萨拉就像球场外疯狂的球迷,突然冲到球场中央,绊倒场上的某个球员。他认为生命就像是一场大型比赛,人类被分为两队——萨拉的队友和其他人,如果输了就要付出昂贵代价,因此每一场比赛都十分重要,尽管他像着魔一样热衷比赛,但他仍然只是个场外观看的球迷,在一群吼叫的球迷当中,大声吼叫着球员听不到的建议,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人在乎他,因为他没有上场比赛,也不会上场在比赛。就像其他沮丧的球迷一样,他顶多能做的,就是突然冲到球场中央,做些违法的行为引起骚动,然后被保安人员拖下场,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有没有被扎到的感觉! 桑德森曾去过堪萨斯大学,然后赴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就读。他常以自己务农的家世背景为荣,但实际上我可以看得出他相当地引以为耻。曾经有一次喝醉了酒,他告诉我来自堪萨斯州的哈尔·桑德森早就已经死了,死在前往纽约的火车上,现在我认识的哈尔·桑德森是在火车停靠于纽约宾州车站时那一刻重生的。 不过通常只有在朗姆酒让他醉到不能自已的情况下,他才会卸下心防,这种卸下心防的机会,少到当他展露出内心孩子气的一面时,会让人觉得怪异,甚至为他感到可悲。他已经离真实的自己非常遥远,似乎早就忘了自己是谁。 她笑了下,“我知道这段关系不会长久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但至少我现在很快乐。”“快乐”,我喃喃地重复她的话,试着为快乐这两个字下个注解,但这个词就像其他像是爱一般的字眼,让我没有办法理解。大部分玩文字的人,似乎对这些类似快乐、爱情、诚实和坚强等深奥的字眼,没有多大的信心,我也不例外。因为跟其他较尖锐批判性的词汇,如混蛋、廉价和虚伪相比,这些字眼太无法捉摸、太难以想象了。我对那些尖锐的字眼比较熟悉,因为它们浅显易懂,容易描述,那些深奥的字眼太艰深了,可能只有神父或是傻瓜才能对它们深具信心。 不过,他的头脑已经被酒精腐蚀,他的整个生活就像是在废油中泡太久而坏掉的老旧机器。 虽然我一直在抱怨圣胡安,却不是真的讨厌这个地方,总觉得迟早我会在这个地方看到不同的风貌,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城市,而你必须待上好一阵子才能感受到它真实的面貌。然而,我待得越久,就越质疑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并不存在这种特殊风貌的地方,或是太模糊以致无法分辨出跟原来的风貌有什么不同。也许,老天保佑,这个地方根本就跟我现在看到的一样——聚集了一堆落魄的流民、小偷和未开化的原住民。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天知道他最后会有什么下场。生命中总会遇到需要稍微让步的时候——不能什么时候,到任何地方,都这么嚣张。” 又扎一次! 如果十年来都是沿用这种看起来居无定所的地址,一个人很容易就被视为命运坎坷的流浪汉,总是漂泊不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待在一个原本就不想待的恶臭贫民窟太久,只因为贪图便宜,我已经受够了,决定抛开一切。如果这种漂泊不定的日子就代表着自由,那我早就已经享受了好多年的自由,现在我做的事也许不那么自由,但至少能够住得舒适多了。我不但将拥有一个住址,也打算买一辆车,另外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事能让我感觉稳定和舒适,我都打算去做。 但这些想象,只是自我安慰罢了,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只想要一张干净的床和充满阳光的房间,而且拥有一些可以称得上是自己所有、等厌倦了再换掉的东西。我不禁怀疑,难道我已经过了那个冲动的巅峰时期了吗?更糟的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悲,只有疲倦和一种与我何干的舒坦。 不时蹦出来的这些跳跃的句子让我想起《项塔兰》里那个黑帮老大不时说出的宇宙真理,那种一边干着混事一边说出让你一震的格言,还真是很有魅力。 下期预告:洛夫克拉夫特《克苏鲁的呼唤》 强尼书叔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ushanz.com/shagk/2260.html
- 上一篇文章: 史上最不靠谱的12场战争,没有刮胡子也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