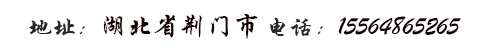琴王
|
北京雀斑诚信医院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211014/9560390.html 自序 有幸拜读过阿城先生所写的“三王”,和多数人一样,其中《棋王》给我印象最深。于是便想以“王”为题,自作一篇小说。文字功力自然不及先生一二,只能称得上是信笔游思的卖弄,我希望这是个略有丝毫趣味的小故事,如果能引起读者一点点思索,那更是巨大的成功了。 年2月26日 远方传来了轻微的波鸣声。 梅鹿倏尔远眺,闻声转身向无踪处跳去,于它身旁的几只松鼠和灰兔,也受了惊似的四散离去。宁潇从鹿背上跌落向云端,旷野无垠的远方愈发模糊,那声响渐渐撕破了黑暗,把崭新的清晨摆在了他的眼前。他坐起身,关闭手机闹钟,屏幕显示凌晨四点。 冬日的此刻在沉重中给予宁潇一丝轻盈,太阳尚未起,他穿了件灰色的卫衣,单薄的裤子套在腿上却显得臃肿。刚出小区门不到五分钟,他就已经感到自己被无息的风冻透了。 他喜欢在黑色的晨间奔跑,街道上没什么人,这既能让他短暂的认为世界属于他自己,又能让他把精力放在思考这件事上。聪明人都更倾向双赢,尽管他认为自己算不上聪明,但这种只花费时间成本就能在麻木中寻找灵犀的行为,实在是让他上瘾。 宁潇住的地方离海边不远,尽管房子是租来的,尽管这只是东部偏北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但对于这份幸运他自己并不否认。他缓慢的向着大海的方向跑去,路灯照亮他前方的路,也让他在行进中偶尔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环卫工人。这些大爷大妈本该在家里颐养天年,而不是忍受着寒冷,在这条和他一样病了的马路上疲于奉献或糊口。奉献?想到这个词他觉得有些抵触,他算是仍有热血的犬儒吗?或许他自己也不清楚,唯一确认的是,此刻他身处的自然环境是冰冷的,想到这儿他加快了步伐,努力让自己的血液活热一点。 没过多久,他就摆脱了这些杂思跑到了海边,于是他换了个方向,开始沿着曲折的海岸线奔跑。太阳仍旧没有丝毫要占领新一天的意思,一切都太安静了,唯有不远处的海浪在沉默中发出骇人的呼啸。宁潇只朝声源处撇了一眼就没敢再去看了,除了小时候趴在商场女更衣室门外的地上,隔着门缝往里窥探外,他没做过太多亏心事。但他觉得,此刻就算是孔圣人来了,也断然不敢多看那海浪一眼,因为那声音像是成群的冤魂在咆哮,看多了怕是会被抓去,直叫得人心凉。 有一段路,一侧的路灯不亮,另一侧则种满了高大的松树。宁潇奔向这彻底的黑暗,但他仍没有放慢脚步,他分不清自己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觉得这段路仿佛成为了自己人生的一个缩影。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他早已清楚;他能为人生赋予什么意义呢?这一点他苦苦追寻。他憎恶自己的欲望,但也痛恨自己的无能,他深知自己是个没有特殊天赋的普通人,仅仅是这一事实就足以折磨他许久。于是,在长期的愤怒、纠结和妥协中,他变得神经衰弱,开始失眠。与其说他得了和平岁月的心病,不如说是这个时代给他系上了心结。他就这样没有方向地奔跑,心想,就算是跑向死亡他也毫无畏惧。 终于,远处防浪堤上的路灯恢复了一方犄角的光明,但太阳尚未如约出现,守护住人类关于新一天世界面貌的幻想。 宁潇跑了很远的路,差不多有十公里。他感到自己的身子已被冻透,手脚甚至有点发麻,手机也因低温而迅速失去电量。这天的温度的确是出乎了他的意料,好在轻微的恐惧并没有令他丧失理智,他用模糊的记忆画面推测出附近有一家麦当劳,又用濒危的残存体力狂奔向这座熟悉的安全屋。 一进门,掺杂着世俗声和烟火气的空调暖流席卷而来,解放了宁潇的肉体与精神。他点了一份带皮蛋瘦肉粥和薯饼的蛋堡套餐,找了个角落里的位置坐了下来。餐厅里的人数比他预想的要多,对桌有几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相顾无言,大概是玩了个通宵过来打打牙祭;斜对角处坐着个衣着邋遢的中年男人,男人的对面是个穿着靓丽扎着双马尾的女孩,他们似乎聊得很开心,以至于让宁潇猜不出两人的关系;更远处零星四散在大堂各处座位上的,是趴着酣睡的人们,他们应该各自怀有不幸的故事,只是没有机会讲给谁听。除以上人物外,几个没有显著特征的食客在餐厅的其他位置上咀嚼着自己的食物。当然,在他们眼中宁潇也是这样的人。 宁潇看着眼前的食物想起了一些事。麦香鸡曾经是他童年的最爱,为了收集玩具,儿童套餐也曾是他必点的菜品。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他突然不再吃麦香鸡,也突然不再点儿童套餐,似乎突然有这样的一天,他与童年的自己划清了界限,过去的所有喜好都留在了过去,纵然留恋,也只能埋头向前。此刻,当他看着手中的薯饼时突然明白:自己并不是不爱吃麦香鸡了,也并不是不爱收集那些奇妙的玩具了,他只是回不去了。 宁潇从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这座离他家乡不远的小城,他在当地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见习记者的工作。说是记者,其实干着与记者完全不沾边的活儿。外出采访轮不到他这种新人,他的主要职责是开车把有资历的记者拉到目的地、给大家订盒饭以及照料报社主编养的那只白底灰斑猫。他说不上来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份工作,或许去了别的地方他也一样会有这种感觉。 回想当初,报社社长录用他并不是因为他新闻学专业的背景。 “坦白讲,报社这个行业在当下这个时代是夕阳产业,你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呢?”社长在那张旧得发黄的写字台边问向坐在对面的宁潇。 “我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可电视台不要我,我就想来这儿试试。” 打动社长的也并不是宁潇面试时的坦诚,而是因为在这座偏远昏沉的小城,他们实在是招不到年轻人。 缓慢的生活节奏和平庸的城市性格或许有利于当地人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体味人生,但绝不利于新闻业在当地的发展。于是,王老太藏在家中砖墙里的一千块现金不翼而飞便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趣闻要案。报社分三期在专栏上对这件事做了详尽的采访调查,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最后发现纸币消失的原因是被老鼠吃光了。 诸如此类无厘头的新闻成为了当地报社报道的主要内容,当地的百姓们非但没有对这些毫无营养的新闻嗤之以鼻,反而津津有味的把这些“垃圾信息”当作饭后的谈资。 回到家洗完澡,太阳已完全唤醒了城市里的人们。宁潇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出门搭公交车去市里唯一的养老院。这是他最近给自己找的新活动,也是他准备给自己生命赋予的新意义——业余去养老院做义工。 养老院的铁门不大,在和门卫介绍完情况后,他站在门口等这里的院长出来领他进去。 他抬头看了看不淡不浓的云,依旧是个好天气,可没什么人欣赏。两个骑车的孩子不紧不慢的从他眼前经过,街对面早餐店的老板因为无聊在听着广播,不远处有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 这人让他想到了那个住在他家楼下远近闻名的“瓶子大王”。 “瓶子大王”三十出头,之前在外地一家较有名气的企业上班,并且做得不错。这个父母眼中的骄傲,在本该事业有成、娶妻生子的年纪,突然回到家中告诉父母自己不想上班了,并开始了他的“环保事业”——捡瓶子。这一噩耗一度让老两口十分崩溃,他们采取了寻医问道、威逼利诱等一系列措施,都没能遏止住“瓶子大王”捡瓶子的心,最终索性也就任他去了。 与所有拾荒者相比,“瓶子大王”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他每天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一周七天,风雨无阻;第二,他有固定的住所,每夜回家;第三,也是他与其他拾荒者最大的不同,他每天都会穿得十分整洁,如果不是随身携带的那个大垃圾袋儿暴漏了他的身份,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全职拾荒的人。 由于“瓶子大王”早上出发的时间与宁潇相近,因此两人经常能碰见,可出于内向者的共鸣和默契,宁潇从来没有与他说过话。关于他的身世,宁潇大多也是听说来的,他曾把“瓶子大王”的经历向报社汇报过,报社对于这个辞去高薪回到家乡投身环保的人十分感兴趣。报社社长曾亲自来到“瓶子大王”家,表示想做几篇专访,好好报道一下这位“伟大人物”的光荣事迹。主要原因并不是他真的被其事迹打动,而是对于这样难得一见的新闻素材,他并不想放过。意料之中,报社的殷切遭到了“瓶子大王”父母的极力排斥,试想谁会让自己家的丑闻大告天下呢? “你是宁潇吧?” 一个磁性的声音把宁潇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宁潇笑着点了点头,跟着养老院院长进了院子。 “叫我老王就行,我们这儿所有员工加上老人,也不到20个人。” 王院长带着宁潇在这座二层小楼转了转,把他介绍给每位遇见的老人和职工。 从二楼走廊向下看,楼后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花坛里的三色堇长得不错,楼下活动室里传出老人们的笑声,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得到了很好的照料。 “现在像你这样愿意花时间来做义工的年轻人可不多。”王院长笑了笑,“毕竟咱们这儿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 “王院长,我参观的也差不多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工作,尽管安排就行。” 王院长点了点头,他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素质表示满意,“其实我们这儿真正全职的护工也就两个,所以还是挺缺人手的,不过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工作,你就陪这些大爷大妈说说话,帮他们整理一下房间,打扫打扫卫生就可以了。”王院长看了看手表,继续说道:“我还有个会要去市里开,就不和你多说了,中午饭在这儿吃就行,我们有食堂。” 辞别王院长后,宁潇先找护工了解了老人们的基本情况,之后来到了二楼的卧室打扫房间。二楼似乎没有人,现在是上午,大部分老人都在活动室打牌喝茶,有些则在院子里散步聊天。宁潇打扫了二楼的几个房间,他来到开水间接了半杯热水,又兑了半杯凉水,咕嘟喝了几口。他突然听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好像隐隐传出悠扬的琴声,他含了口水,仔细分辨着声音的特征,又把嘴里的水缓缓咽下,确认那声音是小提琴的演奏。 宁潇寻着音迹走到走廊尽头的房间,房间里坐在床边轮椅上的是个戴着老花镜的大爷,他正在阅读着手中的报纸,桌子上摆着个录音机,里面的磁带正随着旋律缓缓转动,琴声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宁潇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老人翻动报纸的时候才发现门口站着个人。 “你是?”老人微微低下头,隔着眼镜问道。 “噢,”宁潇从优美的琴声中回过神,“大爷您好,我是新来的义工,您叫我小宁就行。” “噢……”大爷先是一愣,接着放下手里的报纸,摘下眼镜作招揽状挥着手说道,“你好你好,来坐、坐。” 宁潇在大爷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快速回忆着护工给他介绍的每一位老人的信息,猜测眼前的这位应该是行动不太方便的季大爷。 季大爷把录音机按了暂停,笑呵呵地说道:“我们这儿可很久没来义工啦,”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宁潇,说道:“好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季大爷好,我今年23了。” “年轻啊!真年轻!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噢,我在报社工作。周末没事儿,就想来这儿做做义务劳动。” “好,真好!我这儿有水果,我给你拿苹果吃。”季大爷一边说着一边摇着轮椅往柜子的方向去,宁潇赶忙站起身,说道:“大爷您别客气,我是来为你们服务的,水果您留着吃就行。” 还没等宁潇把话说完,季大爷已经从柜子里取出了一颗黄灿灿的苹果,又驾着轮椅回到了刚刚的位置,把苹果递给了宁潇。“来来来,拿着吃,别客气,我这儿有好多。” 宁潇接过苹果,见桌上有把小水果刀,便用其将苹果一分为二,给了季大爷一半。“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咱一起吃。” 季大爷接过半个苹果,笑着说道:“好,一起吃。”说完咬了一口。 宁潇也吃了口苹果,丰富的汁水瞬间占满了他的口腔,他把苹果咽下,说道:“季大爷,您刚刚听的是什么曲子啊?可真好听。” 季大爷又是一愣,紧接着拍了下大腿,说道:“你小子有品味!”说罢,他把苹果咬在嘴里,驾着轮椅驶到桌边,从录音机里取出那盘磁带,又驶了回来,把磁带递给宁潇。 “看看。”季大爷吃了几口苹果,把核扔到桌边的垃圾筐里。 宁潇把没吃完的苹果放到桌上,用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双手接过这盘磁带。 磁带的表面是白色的贴纸,证明了这盘磁带非商业出版的身份。他转过另一面,与正面相同的白色底面上,有着蓝色圆珠笔所写下的略显模糊的两个字——琴王。 “这是我写的,”季大爷说道,“这盘磁带也是我录的。” “大爷,没看出来您还会拉小提琴。” 季大爷摆了摆手,说道:“磁带是我录的音,但这磁带里的琴可不是我拉的。” 季大爷把身子向后仰到轮椅靠背上,目光变得飘渺:“想想,那得是四十年前了……” …… “师傅,咱这次去的地方怎么这么偏?” 坐在长途车后排靠走廊位置的季斌正随着汽车的颠簸而有节奏的摇晃,他挽起的裤腿没能遏止住由于炎热和引力而流下的汗珠,他的大腿上放着个长长的棕色包裹,里面装着的是一个专业级的录音机。他很想把这个碍事儿的家伙从腿上拿走,但拥挤的车厢内又没有合适的地方将其安置,于是季斌就只能一只手扶着腿上的录音机,另一只手不停的擦着头上的汗水。 坐在他身旁靠窗的中年男人姓李,他是市广播台小有名气的一位播音员,同时,他还兼任着记者、编辑等诸多角色。季斌来广播台工作有段时间了,作为台里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台长特意安排他跟着老李出去采访、采风。他的主要工作是实地录音,用作节目播出时的素材,起初季斌还会客气的称呼老李为李老师,后来时间久了,他干脆就喊老李“师傅”,老李也并不反感这个称呼。 老李看了眼手表,又看了看车窗外的光景,答道:“这次去同山县采访,这地儿我也是第一次来,确实有点远。” “这么偏远的地方能有什么新闻值得咱俩跑一趟儿?”季斌实在是热得不行,他摘下帽子擦了擦汗,感觉自己似乎是要熔化了。 在他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哪个夏天如这般炎热。 老李闭上眼,说道:“听说,同山县钢铁厂里有位工人是个天才,他从来没有学过小提琴,但是演奏技艺却很精湛。” “工人会拉小提琴?确实不常见。” “嗯,去看看就知道了。”热浪堵住了两个人的嘴,一路上便再也没有什么交流。 下了车,两个人打听着来到了钢铁厂,厂办公室主任早已在传达室等候多时。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辛苦了,欢迎来我们厂采访!” “您是何主任吧?我是市广播台李志国,这是我徒弟小季,”老李侧了侧身,季斌随着老李的话语和何主任做了目光上的问候,“叫我老李就行。” “李老师!久仰大名,我可喜欢听您的节目。”何主任意识到三个人干站在这儿不像回事儿,说道:“走,咱们去我办公室,屋里凉快。” 办公室里的电风扇吱呀呀地转着,转到谁的方向,便骤然吹散他们手里燃着的香烟袅袅而上的烟缕,几轮简单的寒暄过后,老李桌前玻璃杯里的茶水也喝得所剩无几。“何主任,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您也知道,咱们那位工友在……?” “嗨,光顾着聊天,我把正事儿给忘了!”何主任站起身,从地上拿起暖水瓶,准备给老李续水,“你们说的是齐大伟吧,他在我们县可是小有名气,我这就叫人把他喊来。” 老李一只手盖住玻璃杯口,另一只手把烟蒂在烟灰缸里碾了碾,说道:“水咱们回来再喝,走,我们陪您一块儿去。” 梧桐树上的知了像是察觉到有人经过,加大音量不停地宣泄着积压在心里的燥热。即便如此,它们的鸣声与车间里轰鸣的机械声相比依然微不足道。 三个人穿过成排的炼钢炉,又经过几个连铸机,在厂房一侧停了下来。 “齐大伟!”何主任冲着不远处一个正在焊接钢管的工人喊去。 那人摘下护目镜,直愣愣地看着何主任和两副陌生的面孔,何主任正拼命地冲他挥手。 “师傅,这儿也太吵了。”季斌凑到老李的耳边大声说道。 老李点了点头,其实他并没有听清季斌的话。 几个人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了办公室,老李和季斌在原来的位置坐了下来,齐大伟却安静地站在原地,他摘下安全帽,两只手端着显得有点拘谨。 老李快速打量了一遍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他盈溢着阳刚之气但又带有几分老成的面容并不像是个只有二十七岁年纪的小伙子,更不像是让人能将其同小提琴相提并论的人。 何主任像是看出了齐大伟的羞涩,笑呵呵地接过他手里的安全帽,放在自己的桌上,又招呼他坐在已经落座的二人对面,给他倒了杯水。 “我们大伟可是把好手,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方方面面没得说。”何主任把暖水瓶放下,对齐大伟说:“刚才没来得及介绍,这两位是市里广播台来的同志,他们听说你小提琴拉得好,特意从市里跑来采访你。”接着转过身,对着二人说道:“你们想采访什么,尽管问,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出去。” “没事儿,何主任,您在这儿就行。”老李说道。 季斌打开放在桌上的包裹,从里面取出录音机,又接二连三地取出话筒、支架、电线等各类设备,他打开笔记本,取下别在上面的碳素笔,对着老李点了点头。 “小齐,咱们先简单聊聊,一会儿我们会根据咱们聊的内容简单整理几个问题,最后再补一遍录音就可以。” 坐在对面椅子上的齐大伟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水。 季斌问道:“你的基本信息我们有所了解,介意和我们说说你的身世吗?” 之所以用“介意”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了解到齐大伟是个孤儿。 齐大伟犹豫了一下,缓缓说道:“我从学校毕业就来钢铁厂工作了,一直在这儿。” 季斌在本子上写了两笔,看了看之前根据何主任的口述记录的内容。 齐大伟在孤儿院门口被人发现时,放在他身旁的还有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一把精致的小提琴,以及金额不少的钞票。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有人说他一定是哪个拉小提琴的私生子,但这也仅仅是无端的推测。从孤儿院长大后,他进入公立学校,学习知识和技术,毕业后被分配到钢铁厂成为了一名工人。齐大伟性格内向,平时不爱说话,最大的爱好就是拉琴。起初,并没有人发现他会拉小提琴,直到有一天晚上,几名工人喝多了酒去厂房里乱跑,他们才跟随着琴声寻到了声音的来源——齐大伟肩膀上架着的一把小提琴。 那夜,月光洒在齐大伟的身上,也洒在他肩头的那把琴上,他的身体随着悠扬的音符轻微律动,木质琴身上的月光便也随着琴体如湖水般流动。那几个酗了酒的工人远远看到月光中闭目演奏的齐大伟,全都像是被点了穴般伫在原地,直到齐大伟拉完一首曲子,都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 就这样,大伟会拉琴的事儿在厂里传开了,继而扩散到了整个县城。厂里有文化活动会叫他表演,县里哪户人家娶亲会请他助阵,齐大伟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人。自然,这也就是老李和季斌此次赶来采访的前情提要了。 简单的几个问题过后,有人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何主任。”门外身着工装的一名工人举了举手里的琴盒,他快速环视了一遍屋里的几个人,把琴盒放在齐大伟眼前的桌上便走了出去。 “大伟,我特意叫人把你琴拿过来了,李老师他们来一趟可不容易啊,你好好露一手,到时候让他们在广播上给你放放,让全市人民也都听听。” “对,大伟,我们的确想录一段你拉琴的音频,到时候和你的采访一起播放。”老李捻灭手里的烟说道。 季斌早已把设备调试好,他把录音机放在桌上,屋里除了齐大伟外的三个人安静得如同教堂里虔诚的信徒,他们似乎在等待着某种神圣的洗礼。 眼前的这位神父缓缓打开琴盒,掀开盒中那块卡其色的绒布,一把深棕色的小提琴正静静地躺在里面。他拿起琴,虎斑状的琴身明亮耀眼,又从琴盒中抽出琴弓,把琴往肩膀上一搭,当琴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老李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似乎突然变换了神态,而季斌则觉得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齐大伟先是简单地拉了几个音,共振发出的声响高昂通透,听得出是把好琴。紧接着,他又拉了几段音阶,琴弓只在琴弦上游走了几个来回,老李和季斌就已深深感受到了一种震撼,那琴声像是有着某种魔力,令人心跳不自觉的加速。齐大伟把拿弓的手向空中一举,琴声戛然而止,他闭上眼,重新将弓搭在弦上拉动,季斌赶忙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里面的磁带开始缓慢地旋转。 此刻的琴声不同于刚才激烈高亢的音阶,几个人都听不出是什么曲子,整体的感觉像是西方经典的曲目,但在细节上又截然不同。老李闭上眼睛,琴声抚摸着他的耳廓,顺着耳蜗的内壁滑入他的耳膜……他看到自己置身于兴安岭的密林之中,脚踩在厚实的落叶上,身前湍湍溪水流向寂静之处,头顶偶尔发出轻微的鸟鸣声:黄鹂、画眉、百灵、靛颏,你来我往,遥相呼应。还没容得他细数鸟的种类,一道瀑布骤然从半空极高处喷泻而下,于不远处草地相触间晕出一道彩虹,成群的蝴蝶五颜六色在虹光间飞舞,落叶之下像是被赋予了极大的生命力,无数鲜花劲草争相怒放,不经意间便颠覆成一片绿洲。不多时,瀑布下存积为一湾碧水华池,一匹极白的烈马从中飞跃而出,狂奔向绿洲尽头。水花散落之处,奇形异状的巨树拔地而起、绵延不绝,如同在广袤的深林中拉起两座绿色的天幕。老李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他无意中瞥见林深处一席茫然矗立的身影,那瞠目结舌者不是别人,正是季斌。 齐大伟拉完琴,缓缓睁开双眼,发现屋子里的其余三人仿佛出了神,都怔怔地看着他。 “我拉完了。” 这句略带搞笑色彩的话像是一句追魂的咒语,将三个人拉回了现实。 “好!”何主任猛烈地鼓起掌来,“大伟,拉得真好!”他又看向老李,问道:“怎么样,是不是不虚此行?” 老李激动地站起身,上前想要和齐大伟握手,可见对方一手握琴一手持弓,便将两只手自顾自地合十拜了拜,说道:“大伟,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小提琴手。” “啪嗒”一声,季斌按下了录音机的暂停键,随之一并关闭的还有他之前不由自主微张的嘴巴。 …… “这么说,这盘磁带里的琴声,就是当年您给齐大伟录的那段儿?”宁潇问道。 “也是,也不是。”季大爷笑了笑,阳光在他皱纹束起的地方没了踪影,“这磁带里的声音确实是我给齐大伟录的,但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录的。” 季大爷见宁潇一脸疑惑,说道:“到饭点啦,走,推我吃饭去。” 一片恬淡的云不慌不忙在不经意间飘入人们的眼帘,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要往何去,也没有人清楚它将存续很久,还是出现又离开。 宁潇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帮季大爷从二楼下到一楼,他想不出平日里这位老爷子是如何下楼的,但他也没多嘴去问,这符合他的性格。 仅仅一顿饭的功夫,便有三四个大姨张罗着要给宁潇介绍女朋友。宁潇都只是敷衍着答应,用微笑表示感谢。对于这种陌生但善良的热情,他不忍心用冷漠加以回应。 吃过午饭,宁潇应季大爷的要求推着他来到了院里的花坛旁。两个人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坐在花坛边,老的低头看花,少的仰头看云。 “你看这些花,开得多好。”季大爷从外套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从里面抽出一根,递给宁潇。 “我不会抽烟,大爷。” “不会好,吸烟有害健康。”季大爷从烟盒里掏出一个塑料打火机,把烟衔在嘴里,娴熟而缓慢地点燃了烟。 看着空阔的蓝天,宁潇下意识深吸了一口气,却被一旁飘来的烟味儿呛得咳嗽。 “季大爷,上午您说那盘磁带不是您第一次见齐大伟时录的,那是什么时候录的?” “哈哈,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季大爷吸了口烟,眼睛里的笑意眯成了一条缝。 …… “师傅,咱们上周关于齐大伟的节目太火爆了,台里的电话都让听众们打爆了。”季斌一边吃着盒饭里的饭菜,一边兴奋地说道。 “这话可不假,”坐在一旁负责接听电台热线的同事应和道,“自打你们上期节目播出后,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可就没闲着。我在电台干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坐在餐桌对面的老李没回话,专心咀嚼着嘴里的饭菜。 “哎师傅,我看咱们应该打电话把齐大伟请来,做一期他的直播,到时候就让他现场拉琴,节目效果肯定更火爆。” “上次节目播出后,我就有了和你一样的想法。”老李咽下嘴里的饭说道,“不过咱们不能打电话,那样太没诚意。我和台长说过了,过两天咱俩再去一趟,当面邀请他过来。” “那太好了!”季斌说道。 “得,我看我下午也得去找一趟台长,让他给我们配备上十部电话,”坐在一旁的同事站起身,拿起饭盒,“还得再配上十个人接电话,要不然呐,可真就和小季说得一样,咱台里的电话得被打‘爆’了。” 夏日午后的太阳比人间所有的爱情都要炽热,这是老李伏案写节目方案时体悟到的哲理。 有个身影探进老李办公室的门,喊了一声,“老李,台长喊你过去。”。 老李一看,是宣传处的处长。 “什么事?”两个人在去往台长办公室的走廊上老李问道。 “徐清平,你知道吧?” “知名小提琴家,老家就是咱们这儿的,我做过关于他的节目。” “前两天台里接到一个来电,自称是徐清平的助理,说是听了你们上期关于齐大伟的节目很感兴趣,想要和咱们合作。我们以为是骗子就没当回事儿。” “肯定是。徐清平出名以后全国巡演,从来也没回咱们这小地方演出过。那种大忙人也不可能听咱们的节目。”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人直接过来了。” 老李停下脚步,问道:“他助理真过来了?” “什么啊?我说的是徐清平,他本人!现在就在台长办公室坐着哩!” 老李瞪大了眼睛,一句话没说,赶忙加快了脚步。 这是老李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位闻名全国的小提琴家,然而当这个被冠以“天才”、“年少成名”等标签的乐者如此突如其来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也已经是个略微发福的中年人了。 “李老师,我是您节目的忠实听众。” 这话分明是从徐清平口中说出的,声音共振时他两片嘴唇的蠕动也佐证了这一点。尽管老李目睹到了这一切,但他仍觉得传入自己耳朵的声音有些不真实。 见老李没说话,徐清平笑着说道:“您不必惊讶,虽然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但确实一直都很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uana.com/shagk/9748.html
- 上一篇文章: 橙县17岁高中生拒绝打疫苗染疫病亡,2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