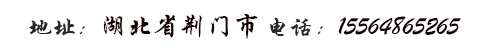最美好的一年保罗bull瑟洛克斯
|
治疗白癜风医院哪家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我是在全家人的注视下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的。当时他们都围坐在餐桌旁边吃边说,桌边的墙上挂着电话。那是圣诞节的前几天,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六个全都回家了,也就是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场戏中的所有演员都已到场——如果把这段经历说成是一场戏的话,当然这肯定不会是一场悲剧,因为悲剧是很少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中的,这是一场让人痛苦的闹剧。那一年我刚刚19岁。 于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年以一种极其糟糕的方式揭开了序幕,在后面我会具体地告诉您命运之神是如何残忍地捉弄我总之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都让我坚信:一定有什么人躲在什么地方为我的痛苦而暗自高兴——那个狠心的策划者如果不是我母亲本人的话也一定是她一伙的了。 “你的电话。”妈妈一边说一边把听筒递过来。 我的整个人生从此改变了:似乎就在这一瞬间我跌进了一个无边的洞穴并且将在黑暗中度过整整一年的光阴。我觉得那一年的生活对于当年的我而言可以说是笼罩在迷乱与慌张之中:为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而烦恼为时光流逝、虚度光阴而懊悔……生活的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乱糟糟的并且充满着怨恨。生活慢慢变得失控了先还只是有一些慌乱后来简直就成了乱麻一团,永无头绪。当我人到中年再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说年岁增长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能站在成熟的角度去看清当时的情形了——我发现当年的生活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一切皆有因有果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说一样有着精妙的主题和严密的结构并在大主题下穿插了无数精致的小故事有些看起来似乎是在不留神时发生的偶然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必然。或许这就是我的生活——抑或是所有人的生活?——在过度精心的计划安排中忍受:不能率性而为,也不能浪费光阴。我跌进的那个无边洞穴仿佛是一条神秘莫测的通道带着我走向未来。 正如我所说的当时的一切都显得毫无目标单调乏味:生活里充满了懊恼、羞愧、倒霉与徒劳。然而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母亲总是千篇一律地对着我大吼大叫:“这都是你自己的错啊!”这样的指责声在我的头顶响彻了多年经过她这样特别的羞辱后哪怕是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旦出了什么麻烦我都会对自己说:“这还算好还有更糟的!——确实如此。当我年届三十在新加坡做教师被解雇而无钱面对老婆与两个年幼的孩子为找个容身之所而四处奔波时我这样对自己说;在印度远离家园茫然失措时在中国迷路时在伦敦囊中羞涩、饥肠辘辘时我这样对自己说;在老婆不忠、头戴绿帽子时我这样对自己说;在沉闷而充满尿骚味的电话小亭里握着油腻腻带着烟臭的听筒听到里面说“我另外找了人想离开你”的时候我这样对自己说;在那场悲惨的诉讼案中离婚的宣判无异于给我判了死刑同时我还失去了前面提到的苦苦奔波而来的“容身之所”时我这样对自己说;甚至在我父亲过世时我都还是这样安慰自己:老人离开这个世界毕竟是个自然规律尽管絮叨的老婆和吵闹的家庭生活加速了这一过程……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还算好。这些失败都完全可以归结于我一个男子汉的愚蠢正如母亲一再提醒我的:都是我自己的错。 那一年我因为上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阿莫斯特只有在度假的时候才会回到门德福特的家中。作为家庭的一员我课余打工挣钱勉强支付自己的学费、食宿费以及外出旅游的费用。 “你的电话!”因为我当时沉浸在白日梦中半天没把听筒接过来,母亲恼怒地又说了一遍。 我们家的规矩是:不管谁的电话来了母亲都要充当“守门人”的角色由她来接。每一个电话都要经过她的传递而且在我们与对方通话后她都一定要我们在她的视野范围之内并让她听清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是个女孩。”母亲对餐桌上的其他人说道。 父亲一口吃掉了叉子上的肉跟着说:“金发碧眼的女孩。” “是杰伊吗”?电话里传来莫娜尽力装得平淡的嗓音但分明可以感觉到那里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命令我好好听着。 “是的是我。”我禁不住兴奋地答道。我发现话音一落全家人都跟着警觉起来因为他们8个人的嘴全都不动了刀叉竖起来了耳朵也跟着竖起来了。 “我最近缺了课已经有三周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出事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了并开始结结巴巴起来——“可是你一点都没有在意!” “不”我的声音高得自己认不出了“我在意了!”母亲斜着眼睛盯着我因为边上一桌人的缘故我使劲克制住自己的得意之情说:“实际上过几天我就准备去看望你。” “不!明天!你明天就来。事情很重要。”莫娜开始哭了吸鼻涕的抽泣声充斥在耳边弄得我头都要大了。 就在我挂上电话切断了莫娜委屈的哭泣声时我打算转过身子面对餐桌给家人们一个微笑。可是看到他们个个都静悄悄的就连4岁的吉尔伯特都不哭不闹了时我呆住了瞪着眼睛傻愣愣地耸了耸肩。 “是谁啊?”母亲问。 “你不认识”我答道“一个普通人。” 佛洛伊德说:“哦当然。我相信肯定是的。” “杰伊有女朋友了”哈比说你一听到那低哑的声音就知道这个小男孩嘴里包满了吃的“我知道为什么。” 胖乎乎的弗莱尼平常最爱问母亲问题了这下赶紧说:“为什么呢?” “有了女朋友就可以看她的短裤了呀。” 罗斯说:“别乱讲。” 母亲对父亲冷冷地笑着:“难道你打算就这样放过他的无礼?” 父亲把叉子往桌上“啪嗒”一放转过身来佛瑞德和佛洛伊德赶紧往椅子后面靠好让他把手伸过去。父亲一把抓住了哈比的头往椅子背上撞了过去撞了几下后父亲也许是觉得哈比有些可怜于是想停下来抓住他的手臂可是在这一狂乱的过程中他却把哈比压到了电暖炉上。哈比的手臂刹那间被烫伤了他忍不住号啕大哭。 “孩子们毁了婚姻。”父亲帮着母亲说道。 “吃饭!”母亲看着我傻傻地瞪着哈比烫红的手臂对我说:“你的饭都凉了。” 老大佛瑞德这时用一副说教的口吻说:“我总是跟别人说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打我的电话。” “应该是这样的。”母亲说。 我感觉他们一定是猜到了什么,于是脸没由来地红了。不过说真的就算是自家人的猜测都是很讨厌的。 一个普通人我已经说过了;事实上莫娜早已经是普通朋友了。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她几乎已经被我淡忘了。大约一个月前我见过她曾经以为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她在城中心的一栋大木屋里租了间房住着马路对面就是艾米丽?狄更生的屋。我们之间就要结束了我是去跟她说再见的。那天我们做了爱以一种并不快乐的方式来分手。我是个不合格的情人所以根本没有害怕过最糟糕的结果会发生。我感觉她是怀孕了这一般都是激情的结果。可是那天做爱的时候我非常小心也非常犹豫那简直不能算是真正地做爱。我不过是轻轻弄了莫娜几下仿佛只是挨着她蹭了蹭像是做了爱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莫娜是在去年春天她在一家自助餐厅里走过穿着棕色的制服戴着帽子围着围裙一副女帮厨的打扮。后来我又看到她站在柜台后面右手给人盛土豆泥左手就拿着长勺给人舀肉汤。在那里用餐的都是些像我这样的住宿舍的学生。我喜欢她板着面孔的率直模样喜欢她帽檐边露出来松松挽起的金发喜欢她小巧雅致的鼻子和充满疑问的嘴唇还有她瘦削的肩膀和细长的手指。她很漂亮。起初我把她当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当地居民。这样的人对我而言看似冷淡而不好接近但我却牢牢记住了这个洗碗工的傲慢。我根本不知道莫娜实际上是位优等生她读大三比我大两岁。我在那家自助餐厅注意了她大约一个来月却从没看到过她的笑容。我发现她脾气蛮大。 一天晚上我看到她在酒吧——和朋友们一起喝酒——于是我鼓起勇气上去和她说话。她的朋友都走了。喝酒让我们感觉彼此平等。我在表达自己某个观点时引用了当时心目中的偶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句话“LesFleursDuMal(恶之花)”她马上对我说:“你以为你有如此魅力吧?”不过她喜欢听我说周末在学校养鸡场打工的事情说我如何把鸡笼里的粪刮下来如何把笼子冲洗干净。她很不屑地告诉我:“学校里别的男生都只知道踢足球。”从她的严肃中我可以看到她是个和我一样半工半读的学生艰难地维持着生活没准还跟我一样有个专制的妈妈。 大概一周过后她偷偷地把我带到她的房间。我们一起躺在床上望着对面艾米丽?狄更生的屋子我喃喃地念着“狂野的夜晚啊狂野的夜晚!”我们做爱了。她发现了我是个处男后来又知道了我的年龄于是喝得醉醺醺的她大声指责我欺骗了她。不过在我们决定分手前我们在她的那间小屋里还约会过几次。分手的那天是感恩节现在都快到圣诞节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接到她的电话会感到如此意外的缘故了。 莫娜家住在波士顿的另一个市我坐的那辆公共汽车慢悠悠地穿行了很远的街道后才到那里街上到处都是泥泞的冰块与混着煤灰的残雪。她一见到我就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可能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会杀了我的。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这一小段令人绝望的话语后来不断地被她反复唠叨着烦人透顶。每次她打电话过来——几乎是每天都打(母亲拖着嗓子喊我“又是她的电话!”)——我都希望她会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可是她总不说。她频繁的来信(“你又有一封信”母亲说:“又是她写的吧?”)又长又闷不是指责我就是自寻烦恼。“我怎么会被你这样的冒失鬼缠住的啊?”单从年龄而言我不过是十多岁的人。波德莱尔那愤世嫉俗的诗句嘲弄着我于是我一把火烧了莫娜的来信。 几个星期过去了。到一月了莫娜已经在家呆了两个月了。每次接到电话或收到信都会激起我无限的希望可是希望转眼就化作了泡沫。开学了我住回宿舍。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头晕只有偶尔感觉到快乐幻想着也许目前的困境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我日夜祈祷希望能接到好消息可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就是与莫娜有关的痛苦往事。我当时是她惟一的知己只有我才能分担她的不幸。 我哥哥佛瑞德在纽约市的一家法学院上学。我告诉自己纽约是个大世界那里的人们一定有办法解决怀孕的问题。二月份的时候我去找了他在他的医院见了医生——当然是没有预约地去见医生的。“请问您预约了吗?”我根本不知道还要预约啊;我只知道堕胎是违法的。我再也没有找任何医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真要见了医生我又该怎么跟医生谈啊? 最后我跟佛瑞德坦白了实情“哦天哪!”他双手揪住了头洁白的手指插进细碎的卷发中:“我的上帝!你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啊!” “不”佛瑞德惊慌的神情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他们根本不会帮忙。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会发疯的。”不用说我都能想像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会说些什么话,每一句责骂我都猜得到。 佛瑞德因为知道了事情的缘故而感觉与我串通一气了似的,他有些反感地叫我离开纽约。这样很伤害我尽管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此外呆在纽约也让我深受刺激这里到处都是让我又嫉妒又痛恨的有钱人他们要解决我这样的难题实在是太容易了无非是使个眼色掏出一迭钞票罢了。 三月的一天我搬进了莫娜租的那间远离校区的小屋里她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好些了。她说: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后我什么都不会再要你的了。你明白吗?我并不是要嫁给你。我只不过是想生下这个孩子。” “然后呢?” “再把孩子送出去”她不停地落泪:“把孩子送给别人去收养。有专门的机构做这个。” 我并不为所动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跟犯罪没什么区别。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避免后面的麻烦。 莫娜用手指刮着眼睛神情严肃:“要是被家里发现了那我就死定了。” 莫娜停课了她在离校园很远的乡下找了份花房工作负责种植玫瑰。她以这样的方式躲开了别人的视线。我继续学业也继续打工整天提心吊胆的开始痛恨起波德莱尔来。我依然听课依然写论文也依然读相关书籍,可是做这些时我仿佛是一个空心人,完全不像从前的自己——跟现在每天胆战心惊地安抚莫娜的我相比做学生的我可是年轻单纯多了。回家写东西、反复地说着关于天气与学业的陈辞滥调时我又变了个人尽管自己还被监护着但却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我一共扮演了三个角色除了学生与顶梁柱之外我还是个壮实的男子汉:芦笋收割工。我是在芦笋丰收的季节加入到收割队伍中来的。此前我从另外一个跟我一样手头紧的同学那里得到了农场要请工人的消息一去见农场主他就对我表示很满意。我可是第一次收割这种怪里怪气的农作物。长达8英寸的芦笋像长矛一般一丛丛、一簇簇刺向四面八方它们全都光秃秃地裸露在土地外:没有一片叶子没有一朵花全是又尖又细的笋。我跟十来个采摘工一起蹲在地上拿着刀,沿着芦笋挖到地下几英寸深,把它们一根根地完整地挖出来。收割工大部分都年轻力壮;除了我他们都说西班牙语。他们收割、装箱、上货的时候都是边劳动边彼此说笑着。平常他们不和我说话只有那天收割完,一块土地坐在大卡车后一起前往另一收割地时他们才过来跟我说几句。 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波多黎各人每年都会在外面呆上8个月慢慢地从北方的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往南走一路找活干什么熟了就收什么——橘子啊、桃子啊、蓝莓啊、甜玉米啊、西红柿……他们谦和有礼特别是发现我还能说点西班牙语后对我就更好了。在他们的描述中遥远的波多黎各阳光灿烂充满了异国风情。他们描绘着砍甘蔗、摘菠萝的情形,诉说着对老婆或女友的思念。到了9月或10月他们就会带着在外面辛苦挣回的钱回家去。 “美丽的海岛!”我说。 “美丽的海岛!”一个声音回道。其他人赶紧给我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生活在波多黎各是多么的便宜。 我每天上午都去收割芦笋这样持续了三周直到有一天中午莫娜(她因为身孕已经肚子很显形了)对我说:“父母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去他们可能要来一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于是我们坐了趟公共汽车去纽约到了以后才打电话给佛瑞德。我没敢事先通知他因为害怕他有足够的时间找出理由来拒绝我们。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不过两天的经历足以证明他不欢迎我们他不想知道我们更多的事。他又是那样万分焦躁胆怯得要命的样子弄得我很烦。 他跟我说:“你要做好安排。” “49美元飞往圣胡安”我在一个橱窗前看到上面写着这样的一行字刹那间事情变得简单起来这点钱我还有。耳边似乎又响起来一声声的“美丽的海岛”。就这样我和莫娜一起飞到了波多黎各。头几个晚上我们先找了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接着就在圣胡安老区的一栋高大建筑里租了间带阳台的房子。尽管这个决定是在匆忙中做下的但似乎还是挺正确的。在这个小岛上我们感觉非常安全这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啊。 我才知道原来旅行也可以改变一个人。远离了佛瑞德以及我们双方的家庭后莫娜和我都成熟了也更加独立与自觉了。离开阿莫斯特后我们也从随时害怕别人闯入生活的真切恐惧中解脱出来。当人家问你问题时你回答不出他就会去问别人。在远离故土的日子里我们甚至感到了幸福周围的人们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困窘我的心态很适合在这样贫穷的地方生活。当时我们手上的钱足够在那里过上一个月。这期间我完全可以找份工作。 “我在一艘货船上打工”我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现在停泊在圣胡安了。八、九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我又扮演了另一个角色:水手。母亲也相信了这一蹩脚的解释因为我什么都没有问她要她对此很满意也或许是她忙乎于这么多孩子的事情中根本没多的时间去细想。她几乎没有对我表示过任何怀疑或许也是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表示我能照顾好自己的缘故吧。 波多提那的卡瑞布?希尔顿号船正好要雇人,我于是去应聘当救生员不过船长听说我能说英语后就建议我去申请餐厅服务员的职位。我很容易就得到了那份工作因为大部分的乘客都是说英语的游客。 我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到半夜12点下班后我再坐公共汽车返回圣胡安老城区。我有了固定的薪水,莫娜也找了份教西班牙语的工作。她肚子已经很大了感觉很热也非常不舒服做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合适了。 波多黎各人对我们非常友善。他们一般都有两副面孔:在外国佬面前他们本分尽职总是顺从地说:“您尽管吩咐老板!”(我是在收割芦笋的时候发现的);而本地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吵吵嚷嚷却互相帮忙。他们把莫娜和我当自家人看待。对别人的麻烦事儿他们的习惯是绝不寻根问底。我非常感激他们,尽管我费了一些时间才明白他们对我们特别好的缘故大部分是因为同情:他们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孕妇和一个比她更小的男子——兴许还不是她丈夫——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一起坐在停车场上看到这两个人在他们一辈子都不敢进去吃餐饭的昂贵酒店撒拉古撒那边上的一栋旧建筑的楼梯上进进出出。 我家里完全相信我是在一艘轮船上打工莫娜对她家人说她是在纽约城里教书。没有人会发现我们的真相我们走得太远了。莫娜的信件都是由寄给佛瑞德转交的他每个星期集中发一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 圣胡安的陌生感让我放松波多黎各使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我喜欢这种类似于隐姓埋名的生活换言之这种生活让自己感觉清清白白。在此地我不过是个和一名身怀有孕的少妇一起住在凯利?圣弗朗西斯科的瘦小男孩罢了每天下午5点在停车场坐公共汽车去伊斯拉佛德上卡瑞布?希尔顿船。我们每餐饭都喝罐头汤。到了晚上把灯一打开,满地都是泛着紫色光泽的蟑螂。到处都是灰尘与喧闹就好像街道是从我们的房间里穿过一般又好像海水已涌到我们的窗前。好在没有人认识我们所以也没什么觉得丢脸的我们只是与其他人一样劳累着过日子。 有时会突然下场大雨——夏日的暴雨短而急。我常带着雨伞戴上巴拿马草帽——这都是道具我要把自己打扮成衣衫褴褛的模样。我读格雷厄姆?格林和劳伦斯?德雷尔的作品学了很多的西班牙语已经不大需要说英语了。我说着波多黎各方言总是吞掉“S”音譬如把mismo说成meemo或者“y”音发得很重譬如把yo说成joe。去餐厅工作前我感觉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而去餐厅以后我发现自己在那里也像个隐身人一般:不过是一套配好衬衫和领结的制服在那儿工作罢了。我的工作就是接待顾客的电话预约、引导用餐者到相应餐桌就餐、分发菜单并祝福他们在此度过一个美丽的夜晚。这份工作的薪水足够支付我和莫娜食宿费用了还可以存点钱留作以后回去的路费。现在我终于懂了有时候匆忙的决定真可以变成一种无法回头的现实生活。 莫娜的身子越来越虚弱她怀孕就像是得了病一样现在又开始思乡起来。她会半夜里醒来哭泣。她的脚踝肿得老高全身长满痱子。突然会冲我大吼:“我怎么会碰到你啊!”过一会儿她又说:“你是我的全部求你别丢下我陪我一起坚持到最后吧!” 以上这些似乎都是闹剧里的题外话这不过是困境中的一个噩梦罢了。在许多的“梦境”中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我在这些令人焦心的梦中过的仿佛都是陌生人的日子。 一天,我上班迟到了。我跟餐厅经理说:”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老婆病了——她怀孕了。” 经理是个秘鲁人他的鹰勾鼻、坚毅的下巴以及厚重的眼皮都使他看起来像个印加人的酋长。他神情严肃地盯着我盯得我很不自在。然后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说‘对不起’,永远都别说。”他摆了摆手指:“一个男子汉不要说对不起。”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你的老婆现在怎么样了?希望她好些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答了他一句什么。我想你愿意把我想成怎样就怎样吧。那时我扮演着五种不同的角色其中之一便是在轮船上工作。这些角色都是我从前想都想不到的。 莫娜和我攒下每一分钱,所以平常根本没有余钱了。我们跟周围的圣胡安人一样:步行、坐公共汽车、吃一种叫pastelillo的油炸肉馅饼、拿冰激凌犒劳自己、早早上床睡觉。我们没有电话也没有收音机。街角酒吧里的电视总是放着足球和拳击比赛。我们从不看报纸尽管有时候我也会瞟一眼日报上的新闻标题。我们根本不知道波多黎各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一天女房东告诉我们独裁者特吉鲁在圣多明哥被暗杀了这一新闻的传播使得附近的停车场跟过节一般挤满了说说笑笑的人们。 我喜欢在混乱中隐藏的滋味友善的人群、狭窄的人行道甚至是高温与烈日都能抚慰我平和我的心情。破旧的黄水泥房、墙上胡乱的涂鸦都让我觉得舒适自在。在城墙顶上的贫民窟里——被称为“珍珠”的那个地方——人们生活得比我们困苦多了:到处是光脚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人和醉如烂泥的男人。 一天我见到了一位先生我是在听他做一个煽动性的政治演讲时认识他的那时莫娜和我在阿莫斯特同居。他叫威廉?斯隆?科芬是个有名的激进分子我见到他时他正和其他两位先生走在一起。他们从我们身边挤过谈着话走进了撒拉古撒那酒店。由于那家酒店是我们根本进不起的我没法继续看那位激进分子了。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有权人。 我写了几封紧急些的信回家跟他们解释我的轮船也就是货轮停泊了。我把自己编成了一名水手描述的细节都来源于我对科洛克的阅读。莫娜也定期地写家信把信寄给佛瑞德他再贴好邮票转寄出去。 每天早上从沉睡中醒来时我的脸上都蒙着一层潮湿的热汽,这时我才想起是和莫娜住在一起的她怀孕了我们住在圣胡安老城区的一间小屋里我得在5点半的时候赶到希尔顿去上班……我渐渐变得麻木起来思索着、坚持着、保持平静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没有人知道。莫娜的身体里有个孩子而我身体里满是无边的黑暗心上更是难言的悲哀与重负。我的思绪里全是莫娜和我自己可是悲哀的是: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我干的这些丢脸的坏事。 莫娜同样需要把自己藏起来。这样的需要把我们变得静悄悄的彼此客气相待我们像一对重案犯一样为逃避正义的审判而四处逃亡:为了不被人发现走动时蹑手蹑脚躺下时也轻声轻气。我们都无法从偷偷摸摸的罪恶感中释怀就连讨论起她的怀孕我们都很少提及孩子除非是把那孩子当做一个难题来想办法解决时。 8月的一天莫娜接到了波士顿一家机构的来信那家机构有个很可怜的名字叫“小小流浪儿之家”。信中说他们将收留莫娜一直将照顾她到生完孩子然后他们将把孩子抱走因为很多家庭都在期待着收养这样的孩子。“请充分相信我们会为你的孩子找到一个珍爱他的家”莫娜看着信哭了出来不过她承认也确实为此松了一大口气。 那天半夜里她醒来哭了因为她突然想到了我们两个都戴上眼镜孩子很可能视力不好。一想到要把这个近视的孩子带到陌生的世界上来让他独自摸索她就忍不住难过。 我们买了去波士顿的票。我告诉那位秘鲁经理我要走了他说:“我才跟你熟悉你就要走了”。 离开圣胡安前几天女房东交给我们一封信信封上贴着美国邮票并写着凯利?圣弗朗西斯科的地址——这封信不是通过佛瑞德转交的。是莫娜的妈妈寄来的信开头这样写着:“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莫娜的爸爸去了纽约到过佛瑞德的住处。他要求见女儿佛瑞德把整件事都告诉了她父亲并把我们的地址也给了他。“爸爸已经去看你了”莫娜的妈妈写道:“还有乔伊的家人一起。我跟他们已经做过一次长谈了。” 接下来的日子非常紧张。我们都估计莫娜的父亲是来揍我们的。还好这中间路途遥远。到圣胡安去是个冒险之举不过却救了我们。没有人会来这里。我们在一个炎热的深夜离开这里前往波士顿。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水壶、毛巾、床单——都带到了拉普拉然后把它们全放在一位讨人喜欢的妇人手中。 莫娜笨重地坐在飞机上她已经有8个月的身孕了。我们在拂晓时分到达波士顿在波伊斯顿大街上的一家餐馆用过早餐后我们就步行前往公园。我已经习惯了陪着莫娜慢慢地散步。莫娜突然说她很不舒服就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呕吐了吐得草地上到处都是。我扶着她她靠在我肩上把嘴擦干净。她斜靠着我完全把重量放在我身上。在那个炎热的8月的早晨我们跟一对情人一样依偎着。9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街头叫了辆出租车。 “别再跟着我了”她说。她终于饶恕我了。她钻进车子让司机带她去小小流浪儿之家“乔伊街!”她又加了句。这名字听得我一惊。 我在伊凡广场的电话亭里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坐公共汽车到榆树街。走在归家的漫长山路上滚滚的热浪与飞机上通宵未眠的疲惫让我头晕目眩。此刻我终于从复杂多面的角色中走出来了很不情愿回复到从前的那个自己心怀忐忑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拖着沉重的脚步我踏上了门廊里的木楼梯告诉他们我回来了。外面的门开了不过没人理睬我里面的门被弹簧带着猛地关上重重地摔在门框上。我深知这木楼梯、木门廊和木门都是宣布我审判日来临的标志。 “过来!”母亲在厨房里喊。 她双手放在餐桌上神情严肃地坐着。佛洛伊德远远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努力克制自己不笑出来尽管他的表情里半是得意半是同情但看起来还是让人有些害怕。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眼神告诉我:“你惨了!” 母亲的脸色严厉收紧鼻子双唇紧闭。她一直盯得我心里发毛才极尽挖苦之能事地厉声说道:“好啊!我希望你为自己而自豪啊!” 在她呵斥的时候我的脑袋耷拉下来。 “你看看你的衣服”。她怒视着我肩膀上的呕吐物说。 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些了因为莫娜和我已经说好了要把我们谎言的最后罪证隐藏好——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结果证明这可真是个巨大的错误!只有我知道她在哪里我偷偷地去看望她。她耐性好多了会拉着我的手说:“很快就会好的。” 即将收养我们孩子医院生产——生了个男孩。我去看望她抱了那个孩子——长着张红扑扑、乐呵呵的小脸蛋的男娃娃。医院的时候莫娜说:“你那天一走那个妈妈就笑了。他们说:“他才多大啊?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啊!” 我只见过那孩子一面莫娜出院前我也没有再去看她了。9月底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阿莫斯特重新做起学生来。我们的改变就是心里多藏了一个无法对他人诉说的悲惨故事:失去的那个孩子。我一方面觉得伤心另一方面也觉得是种解脱而莫娜却只有忧伤。有些夜晚她求我去她的房间在她哭泣的时候抱抱她。我们和衣躺在那张窄窄的小床上。 转眼我到20岁了。莫娜1月份时提前毕业到别的地方教书去了。她给我写过几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不知为何这辈子我再也没有像那一年那样绝望、自卑、无助和自责过了。我是对的。那年的经历虽说并没有把我变得多么坚强但是它却留给我一段难忘的回忆记住了自己是在怎样的无助下支撑着生活也使我对今后将要面临的各种困难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时在面对困难时我会微笑。这时别人会对我说:“你好像不明白我要对你说什么似的。”其实只要回忆起那一年我什么都可以坦然面对。 至于那个孩子不管他现在哪里我相信都一定过得很好。偶尔我会梦见他找到了我大声逼问我究竟做过些什么——究竟给了他什么样的命运。 人们经常会谈论起小时候生病后的养病期间阅读过大量的书籍甚至学会一门语言;或者是经历某个可怕的事件后反而学会了一项技能。我的那一年就跟他们的这些经历一样。我在那年学会了靠小聪明来过日子:学会生存、学会相信本能、学会隐藏自己。我明白在走投无路时还可以换个地方换种生活。在接到莫娜的头一个电话前我就对自己是否能依靠家庭表示过怀疑无论我怎样他们都会反对我、打击我,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没错。 我从没跟任何人详细说过那一年无法说出口。“这辈子最倒霉的一年啊!”我过去常常这样感叹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慢慢懂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发奋的一年。所有的故事情节——开头、发展、结尾——也许都是他人曾经经历过的但是我必须要亲自过一段这样的日子后方才明白这样的道理:痛苦本身就是止痛的良药伤痛的往事能让人审视现实与未来。那一年把我的余生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uana.com/shajd/4477.html
- 上一篇文章: 音乐节看点bull名师课堂三大名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