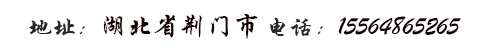日本人为什么喜欢和墓地住在一起
|
北京哪能治疗白癜风 http://m.39.net/pf/a_4784099.html 来源:那一座城(thecity) 过年的时候, 城君去了一趟日本, 路过京都的居民区时, 发现不少楼房旁边都毗邻着一片墓地, 四尺见方的一小块地, 上立墓碑,刻有家纹, 墓碑前插着一些细长的木板, 是象征着佛塔的“卒塔婆”, 每年忌日亲人从庙里请一只, 年头多就簇成了一堆。 周围零散矗立一些雕塑, 上面雕刻了各式的佛像。 不时有三两人在其间若无其事地散步, 仿佛自家后花园一般。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 墓地和阳间阴阳两隔, “那边”是阴森、冰冷甚至不祥的, 断不可以和生活离得太近。 那么是怎样的生死观, 让日本人可以毫无负担地 和“魂灵”亲密接触? 其实与墓地同居一开始并不是 他们主动选择的。 在江户时代, 日本为了阻止基督教在日本的大肆传播 挑战佛教的地位, 设立了寺院与信徒的关系维系制度。 那时在一座村庄里, 很多时候只有寺庙主持会识文断字, 掌管着村民的一切。 村里只要有人去世, 必须也只能埋在寺院内。 因此日本寺院及周围, 开始有了很多坟头的雏形。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 一场空前的灾难席卷了东京和横滨, 地震和火灾损毁了大量建筑。 震后土地重新规划, 东京都政府和寺庙达成协议, 重新分配了拥有巨大土地的寺庙, 顺带也影响到了墓地的迁徙, 寺庙可以在城区保留小块墓地。 自此之后, 寺庙里的墓地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块, 慢慢形成了城区里随处可见的墓地群。 可能也是由于这样的演化过程, 使得城市里居住的人们习惯了 居所旁边有另一个世界邻居的陪伴。 其实最早时, 蛮荒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 死与生的辩证关系, 墓地的选择无外乎像今日 处理废弃物一般随处安置, 七零八落中可能早已忘了先人在何处。 随着智力的开化以及宗教的介入, 死亡才开始有了值得祭奠的意义。 后来随着城市的规划, 墓地再一次被人们有选择地布置。 阴间的世界, 其实一直由阳间的你我支配着。 世代多灾多难的日本人 很早就领悟到人生的短暂, 将佛教作为人生信仰的他们, “向死而生”是深深植根在心底的信念。 家中亲人去世, 葬礼中几乎不见放声大哭的情景, 多数人只是平静地默哀。 《挪威的森林》里说, “死亡不是生的另一极, 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存在。” 在日本人眼中, 死后便会成佛, 灵魂便能成神, 越靠近墓地, 灵魂就更容易受到神佛的保佑, 是件很幸运的事。 如果说开罗屋顶的墓地家园 是穷人们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日本人和墓地为邻 早已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祈愿。 在很多西方国家, “墓地旅行”早已成为新风尚。 巴黎的拉雪兹公墓里的王尔德墓碑, 被各国的女性仰慕者印满了唇印; 危地马拉的奇奇卡斯特南戈彩色墓园 被涂上了玛雅人喜欢的色彩; 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公墓俯瞰加勒比海, 海浪经年地拍打在脸庞, 风经过时吹起唿哨, 埃尔莫罗的孩子们放着风筝跑过...... 他们对死亡纪念的重视 远远超过出生时的庆祝, 因为他们相信 “人出生时还什么都不是, 只有死亡时人生的意义 才会完整地显现。” 我们国家也有人正在身体力行地 消解着人们对死亡的偏见。 北京师范大学的陆晓娅老师 讲授的“影像中的生死学”这门课, 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 每年清明节前后, 她都会带学生去万安公墓走一走。 她教学生用碑文作为生命的索引, 想象墓主拥有的人生。 把死亡这个生命的隐形伴侣约出来, “活着”就有了一个坐标。 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想随她去寻访墓园, 她甚至地想开辟一个新职业:墓地导游。 她相信和墓园里中的安睡者对话, 能听到那些闪光的人文思想绵长的回声, 更能获得在逆境中隐忍生长的力量。 死亡,总是和信仰安放在一起。 西方人把墓地寄托给教堂, 日本人将墓地交付给寺庙, 而我们, 又将墓地托付给了哪里? 那幽幽的松柏中, 真的有我们的心之安处吗? 虽然已经有了陆老师这样的先行者, 但距离我们真正与死亡和解, 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ND-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uana.com/shajd/5200.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终一战,草帽海贼团各自的对手是谁路飞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