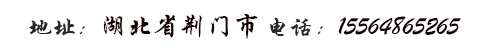新冠病毒疫情与合同ldquo不可抗力
|
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以武汉为“震中”的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事件”。由于防疫隔离需要,很多企业运输网络受阻,供应链中断,甚至停产或停销。 这次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如何管理受影响的企业可能的违约责任?对涉外合同的当事方来说,因为不同法域对“不可抗力”或者类似制度的认定标准不同,这个问题就更复杂。比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以“不可抗力”为由向几家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提出延迟履行合同,而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就明确拒绝中国天然气采购商发去的不可抗力通知。 本文将在中国《合同法》、美国普通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框架下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提供建议。本文为普法公益文章,可能被视为包含法律服务广告,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法律意见。 首要问题:合同“有约定,从约定” 英美法系下的合同法奉行“意思自治”的精神,交易中的各种安排原则上由各方自行协商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所以,如果合同中有“不可抗力”条款,应按合同约定执行。但是常见的“不可抗力”定义列举地震、海啸、飓风,或者战争、罢工、禁运,却不一定提及流行疾病疫情。这种情况下,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可否援引这个条款就取决于本次疫情是否符合合同中“不可抗力”的一般性定义?解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合同的定义本身以及对定义语言的解释。 如果合同中没有定义“不可抗力”,或者虽然有定义,但列举项中没有特别提及流行疾病疫情,就要依靠合同法的规则来填补合同空白(gapfilling),为交易方提供公平的风险分担机制。遗憾的是,全世界的众多法域中并没有完全统一的“不可抗力”认定标准。好在本着自然法的公平正义理念,总体上说,许多制度可算得上是殊途同归。下面我们分别讨论。 大陆法系“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 “不可抗力”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源于大陆法系(英文“forcemajeure”一词系借自法语),最早见于法国民法典,后逐渐被其它国家接受。各国法律对这个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法国民法中,一般认为构成“不可抗力”的因素必须(1)无法抗拒、(2)无法预见、(3)存在于义务人之外(不受义务人控制)并且(4)致使合同在根本方面无法履行(注意:不仅仅是履行存在困难或者履行成本大幅增加)。 中国《民法总则》第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按该法规定,不可抗力具有“三不”属性——不可预见(unforeseeable)、不能避免(unavoidable)、不能克服(insurmountable)。中国《合同法》第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实践中,有些英文合同在定义“不可抗力”时也采用这种“三不”要件。 英美普通法的“履行不可能”的发展演变 在英美普通法传统上,具有类似“不可抗力”功能的制度之一称为“履行不可能”(impossibility)。这个规则起源于年的英国经典判例Taylorv.Caldwell,其中被告音乐厅的主人被法院认定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为音乐厅在交付给原告承租人之前不幸毁于一场火灾,既然被告已丧失了履行合同的能力,迫使其继续履行既不可能也有违公平。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个制度已经被“履行不现实”(impracticality)所取代。简单来说,新的规则并不要求义务人完全无法履行,而是放宽了认定标准,只要继续履行已经“不切实际”(impractical),义务人就可能被免除责任。 在这个规则下,美国各州法院通常要求义务人证明: 1、有某种特殊情况(specialoccurrence),它一旦发生就会导致合同履行极为昂贵或者困难; 2、双方最初订立合同的时候做出过基本前提假定(basicassumption)——某种特殊情况不会发生(这里不是指纯理论上的绝对的可能性,否则这个要件也就丧失意义了。此处实际上要求的是在具体情境下,某种特殊情况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并且对那种特殊情况导致的风险承担没有约定; 3、与双方的预设假定相反,某种特殊情况确实发生了,并且导致合同履行遇到阻碍。 在前面音乐厅案的语境下,就会是这样的分析: 1、火灾将音乐厅付之一炬,被告在履约日之前完成重建音乐厅的现实可能性不存在; 2、双方签合同时预设音乐厅不会发生火灾,也没有约定如果发生火灾谁来承担风险; 3、与双方假定与预想相反的事实是:音乐厅在交付承租人之前毁于大火。 以上三个条件均满足,所以法院免除了出租人的履行义务。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章的“履行不现实”制度 《统一商法典》第2章(theUniformCommercialCode)管辖货物买卖,在美国全境除路易斯安那州和波多黎各以外都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虽然各州都对其作了部分调整。这部法典是美国案例法法典化的产物。它放弃“履行不可能”,采纳了“履行不现实”原则。 该法典第2-615条“失去[履约]预想[前提]条件时的免责”(a)项规定:“如果由于发生了订立合同时作为[履约]基本前提条件[并]被假定不会发生的特殊情况,或由于卖方因善意遵守了外国或本国政府法令(不论此种法令以后是否被证明为无效)而确实难以按约定方式履约,……卖方即使延迟交付,或部分地或全部未能交付,也不构成违反买卖合同义务。” CISG中的“履行障碍”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InternationalSalesofGoods,简称CISG)的规定。CISG第79条第(1)项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这里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障碍”(impediment),而且没有使用任何可能与其它法域建立关联的术语或表达方式,据说是特意为了保持中立,从而使得其更加“国际化”。根据起草者的描述,这个条文的主旨在于“仅仅免除物理或者法律上履行不能(physicalorlegalimpossibility)的责任,而不是由于情况变化导致履行困难。 ” 总结一下,这个条文对免除合同责任要求三个条件: 1、义务人不履行合同是由于超出其控制的障碍; 2、义务人在缔约时无法合理预见这个障碍; 3、义务人无法避免或者克服这个障碍(或者后果)。 显然,这基本上就是大陆法系“不可抗力”要件的翻版。但是,引发争议的是,CISG第79条的适用范围如何?是否覆盖前述美国法上“履行不能”和“履行不现实”这两种情况,还是仅仅覆盖前者?有学者认为,从这部文件的起草历史考察,应该仅限于义务人完全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况,而不包括履行困难(hardship)——即履约在经济上不可能(economicimpossibility)或者商务上不现实(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uana.com/shazy/8170.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国的极化不会停止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